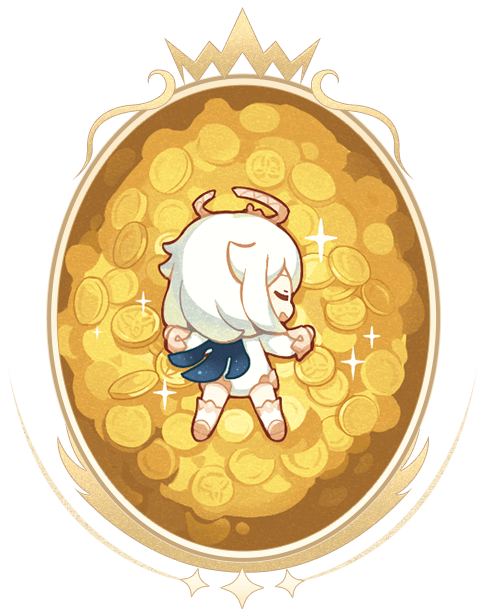You want to favourite this post:
看時代革命哭了兩個半小時,從梁凌杰之死開始就掉眼淚,感覺不到情緒,只是身體裡有水分想要一直流,一直流出去。那位赤手空拳在前線與警察對峙、大喊「我不想這裡變成八九六四的天安門廣場」的母親,那天她說,你們也有小孩,為什麼要這樣打這些小孩?我不是衝擊你們,我沒有武器,我也有付出代價。然後她被警察暴力擊傷,一路哭喊由同路人帶離衝突現場。事件的影片和截圖在微博和朋友圈引發了一定的聲量,很多過往可以理解為「政治冷感」的友鄰們在當時都表達了關注和憤慨。我一直記得。
電影裡有年輕的抗爭者說,很多人講是時代選擇我們這一代人,但其實反過來說,是我們這一代人做了我們的抉擇。我做了二十多年人,沒做過一天的共產黨擁躉,可是那一刻回望這三年,變得越來越痛苦和激憤,我才清晰意識到心底那份血海深仇是來自哪裡。八九六四,過往種種,究竟是核爆後的碎片,觸目驚心而已。香港革命、新冠肺炎、傳媒業淪亡,眼睜睜看著極權無下限地摧毀公共良知的水位,這一切才是我的時代、我的真實、我的血債。那些走上了街頭便不能再回家的年輕人,那些背著沈重的書包奔逃過警棍和 tear gas 的中學生,那些在理工大學的下水道看不到去路的抗爭者,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,他們也都付出了代價,像《親愛的黑色》裡唱的:「花貓也沒了,單車也沒了。寫低的便條亦再沒文字了。」他們是真正的義人。而我甚至不敢質問我可以付出的代價是什麼。在這個時代,我的 position 是什麼。這一刻我已為說出這些話的自戀嫌疑所羞愧不已。
六四前夕我去參加本地一個廣東歌 busking ,在一個小型的露天廣場聚集了數百人,連商場的二樓也都是手機燈。我們齊唱風雨中抱緊自由,唱狂雨暴雪一起對抗。我發室友看,她說,年輕人需要一些公路感。當下我心中一念,年輕人需要的是集會感。其實很荒謬,就像李佳琦的直播一樣,在絕大多數人的心中那只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市民文娛活動。但在這一點點荒謬的感動當中,我知道人群裡一定不只有我在音樂中解讀出共同的記憶、信念和意義。很慚愧我無力抵抗什麼,只是無時無刻不在浮沙中掙扎著。